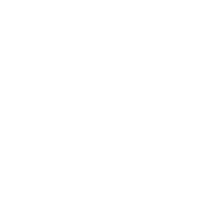也許是因了愛詩的緣故,我最早知道季羨林先生����,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。那個時期��,讀書市場還沒像后來這樣的開放�����,我記得自己不論是到哪里��,總是毫不吝惜地購買書籍,尤其是詩歌方面的書籍?��,F(xiàn)在已記不清到底是什么時候����,在什么場景之下買了一本《羅摩衍那》���,該書店僅有的一本���。我知道了他的譯者是季羨林先生?����!读_摩衍那》是印度人民的國寶����,被稱為史詩,最原始的詩��,可是�,實話實說,捧著它閱讀�,我卻進不到詩的境界中去���,無法領會其中奧妙。倒是里面的插圖讓我產(chǎn)生興趣�,記得作者好像是秦龍先生。迫于生計�,我在西安這座古城中數(shù)次搬家,數(shù)次丟棄物什�����,今天寫此篇文章����,想將《羅摩衍那》找出來翻翻�����,怎么也找不到了��,由此也可知我對這本書的愛惜與否了����。
真正對季羨林先生有所了解時,已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后期�,也是因了一本書——《牛棚雜記》�。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���。該書在封面上赫然打出:“這是一本用血換來的/和淚寫成的文字/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后代的/最佳禮品”���。對此做法我不加任何評論,但作為執(zhí)政黨的最高學府的出版社能出版這本書�����,卻使我感慨萬分�����,既為時代的進步高興�����,也暗暗慶幸我們國家的未來充滿了光明����。書印得精美,季老質樸的文字更讓人著迷��,內中雖然時不時地出現(xiàn)不和諧的音符��,但季老的愛國之情溢于言表,我記得在《我的心是一面鏡子》的最后一段里����,季老這樣寫道:“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: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(東方文化的核心)復興的世紀。”振奮人心�,能解在多事之秋里我等生成的苦悶的情結。我是一口氣讀完這本有血含淚的最佳禮品的��。
寫到這里����,有一件事不能不提。在1998年的年底����,我為供職的報紙寫了一篇《閑話九八文壇》的文章���,其中有一段與季老有關�����,小標題是《季羨林〈牛棚雜記〉后》�����,如此這般寫來:季羨林先生已是名副其實的“國寶”了�。1998年,季老先生可算是領盡風騷���。年初《牛棚雜記》出版���,驚動文壇上下,以其“用血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”使讀者動容���。年末����,香港鳳凰衛(wèi)視“楊瀾工作室”對老先生的專訪�����,更是風光無限�,讓觀眾領略了老先生侃侃而談的風采。當然�����,老先生也有口誤,那句“時隔30年����,我還是不敢告訴農民我的工資數(shù)目,怕說出來讓農民笑話”��,若老先生不講出自己工資一個月下來“就是個兩千吧”也許沒什么��,偏偏他講了出來����。我想,農民不會笑話�,只會邀請季老先生“方便時下來走走”,不然���,他們會說“您老‘瓤人’(陜西方言�,意在挖苦�、諷刺對方)哩”。這段話�,是我在過去時唯一的寫有關季老的文字���,留存于此����,豐富本文。
寫了這么多��,似乎還沒進入主題���。這篇文章的題目“季羨林與《山河永戀》”���,并沒有多少深刻的含義。季老寫下的“山河永戀”這四個字�,是為周明先生的著作題寫的,據(jù)周先生講�,季老同時寫了兩條供出版社選用,后來將其中一條送給了周至鄉(xiāng)黨王殿斌�����。周先生見我熱衷于收藏�,也寫了一些關于收藏的短文,便許諾將季老的另一條題字贈我留念���。季老的手書還未得到�����,我卻有了寫這篇文章的心思����,一則提醒周先生別忘了曾有的許諾,二則在讀過季老的其他著作后�����,對老人家多了理解�����,為當日的無顧忌地放言感到愧疚?,F(xiàn)在想,當時季老對實時的了解��,大概多從媒體知道���,而媒體的報道又有多少事是不含水分的呢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�!長篇報告文學《中國農民調查》中記載有前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曾上當受騙的經(jīng)歷����。一個老者、僅是一介書生的老者��,難道你要求他什么都能弄明白��、弄清楚嗎�����?��!這也是我上面全文引用曾經(jīng)寫過關于季老的文字的原因����,立此存照,以省自身�,也給讀者提個醒。
山河永戀����,我想,每一個有良知的中華兒女����,無論身在何地�,都應該時刻眷戀祖國的大好河山��。周明先生的《山河永戀》����,是用他手中的筆、用他那永無休止的熱情��,為我們寫下了許許多多中華優(yōu)秀兒女愛國�����、愛人生的篇章����。他用樸素的筆墨、真摯的感情��,以他那特殊的經(jīng)歷�����,為我們記錄下一個時代里的一個特殊群體的生活性情����、人格魅力和理想境界��,在這部作品中,收錄了他散見于報刊的文章120余篇����,記述的文壇人物也有百余人,其內容既有現(xiàn)實的作用�,也有史料的價值。難怪讀過周明先生文章的人�,都會豎起拇指說:“周明先生被譽為中國文壇上的基辛格問心無愧,他是中國文壇的活詞典���。”